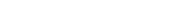原标题:虚拟现实:促使人们与原有生活方式决裂
2016年年初,我收到了美国朋友寄给我的Google Cardboard。那是一款结构简单、造价低廉的VR头显。戴上了这个看上去略显粗糙的小家伙,我获得了自己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体验:浸入式地观看了《纽约时报》于其网站和手机应用上推出的第一条VR新闻《流离失所》(The Displaced)。这条新闻给我留下的最直观的感觉就是眩晕,其次则是迷惑,后来,各种负面的情绪渐渐退去,我才感到兴奋。我清晰地意识到,2016年对全球文化的发展将是至关重要的一年,这个名叫“虚拟现实”的东西则会扮演独领风骚的角色。
如今已是2016年年底,尽管VR头显的眩晕及高价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彻底解决,且相当数量的中国人或许根本没有摸清这个“虚拟”出来的“现实”究竟是什么东西,但这一切无碍于全国VR硬件市场规模在一年中以几何级速度蹿升至逾20亿元,涉足VR技术的创业公司及相关领域公司则达数百家。包括高盛、TalkingData在内的知名咨询机构均高调而乐观地宣称:未来是属于虚拟现实的。
在当下的中国,作为产业和技术的虚拟现实仍面临着诸多发展困境。但对于文化的观察者来说,搞清楚“虚拟”出来的现实和本意的“现实”之间究竟关系如何,恐怕已成为当务之急。正如《纽约时报》VR项目的负责人Jake Silverstein所强调的“虚拟现实让记者挣扎于新闻是什么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如何做新闻的问题”,对于所有对虚拟现实技术有浓厚兴趣并坚信其将改变社会文化生态的人而言,这场以“虚拟”为名并致力于为“虚拟”正名的认知革命,对人们与外部世界之间关系的影响,或许与电报、电视和互联网曾经带来的文化地震都不相同——它正在改变界定人类文化价值与形态更本质的东西。
虚拟现实对于新闻业的“进攻”是直到2015年才有的事。在此之前,这种技术已在游戏、培训、会展等领域得到了广泛运用。不过,是“虚拟现实新闻”的出现才让人们陡然意识到问题所在:因为新闻所应承载的东西只能是现实,若这一现实是被“虚拟”出来的,那么新闻还是新闻吗?比虚拟现实新闻更令人瞠目结舌的,则是借助虚拟现实技术实现的“真实的”物理接触。一家位于日本的虚拟现实企业甚至于今年4月研发出了一套能够令使用者得到性体验的穿戴装备。有人预测2020年人类社会将可以在技术上完全实现消弭一切身体接触。我想这或许就是那只简陋的Google Cardboard最初带给我眩晕和迷惑感的原因。它有能力改变我们已经拥有或正在经历的太多东西,而我们甚至没有为它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的时间。
对中国人乃至全世界的人来说,2016年都是相当魔幻的一年,方兴未艾的虚拟现实技术毋宁说是对这种魔幻感的预告。耐人寻味的是,中国人在这种本应令人措手不及的技术与文化变动中,似乎显得格外兴奋。某知名市场研究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不但2016年全球在虚拟现实领域的总投资中有超过一半来自中国,而且中国人对虚拟现实技术及设备的兴趣也远远超过了西方人。这样的现象可以用“中国人对新技术更为热衷”这样简单的逻辑来解释吗?如果不是,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解释?
作为一个过去一年中在欧洲生活了大半年、在中国生活了小半年的中国人,我的体验是:中国人似乎更容易适应原有逻辑被破坏掉的新生活方式,也似乎更容易义无反顾、毫无惋惜地与原有的生活方式决裂。这仿佛是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两种趋势相互博弈的情境下,中国独有的一种文化心态。所以,就如虚拟现实技术“虚拟”出来的那个“现实”一样,虚拟现实给人的心态带来的冲击,也成了一种被塑造和建构出来的幻象。坦率地说,任何一种技术的狂飙突进,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都不能算新鲜事,但面对那些或许将改写生命与生活的本质的东西,人类一味以审美的方式去享受其带来的眩晕感和魔幻感,这恐怕是比技术本身更令人惊惧的现象吧。(常江:文化学者)